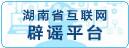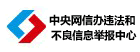《方言里的乡愁与魅力》(散文)
作者:李陵湘 播音:陈 欣
方言,是地方的“特产”,它承载着一方水土的风土人情,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。初听各地方言,往往如同听天书,一头雾水,然一旦有人稍作解释,便如梦初醒,觉得其中别有一番风味。 小时候,我常听长辈们说“五里不同音,百里不同俗”。长大了方知其所言不假。我是个矿二代,矿山地在茶陵,而茶陵话与矿山话区别很大,说白了听茶陵哥们用方言聊天,初听如鸟啼风语,再听似懂非懂。
比如茶陵老乡说:“今尼(日)娥(我)上街,哞(见)到你郎心(女婿),背甲细噶几(背着小孩)。娥(我)问几(他)你旁娘尼(老婆)乍嘎冇来(怎么没来)?几哇(他说)俩银(人)走到半路,遇到婶几(婶婶)。婶几哇(说)瘦几(叔叔)病嘎哒(生病了),几(她)陪婶几(婶婶)切(去)镇上抢(请)医生了……”若无人解释,这段话确实像天书一般,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可一旦有人点拨,便能明白其中的趣味与生动。
我是正宗的湖南人,祖籍湖南双峰,但并非在双峰出生。我的父母都是双峰人,上世纪 50 年代,他们离开家乡,来到湘赣边的茶陵湘东钨矿工作,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工。早期的湘东钨矿还是私营的,后来收归国有,父母便成了矿山里吃国家粮的正式职工。钨矿在建国初期是国家开发的重点矿山,从全国各地抽调了许多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支援矿山建设,同时也面向社会招进了几千名矿山工人。冬去春来,许多矿工在矿山成家立业,繁衍出像我这样的矿二代。
矿山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,乡音也是百花齐放,各有不同。特别是对父母的称呼,更是让人眼花缭乱。我们这些矿二代,从小青梅竹马,虽然祖籍不同,但同生一地,便有了一个共同的“籍贯”,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体系。同一个意思,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达方式。比如在对父亲的称呼上,既有特性,也有共性。特性是家传的,第一启蒙人是父母,这个称谓带有典型的地域色彩。
比如在我家,称父亲为“波波”或“爹爹”(发音是“的的”,和的士的“的”同音),这个昵称相信许多人听了会一头雾水。而其他发小对父亲的称呼也是五花八门,在家里有叫“牙牙”“牙老子”“牙老倌”“爷爷[ia·ia]”“爷唧[諬]”“爹爹[tie·tie]”“爹爹[ti·ti]”等等。出了门,为防止别人听了晕头,所以在其他场合和圈子外的人交流时,我们都会打官腔,统一口径称父亲为“爸爸”。
母亲的称呼也各不相同,“妈妈”“娘”好懂,但也有人叫“嗯嘛”。这些称呼听起来或许有些奇怪,甚至会让人忍俊不禁,可这正是方言的魅力所在。方言就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,虽然形状各异,但却都散发着独特的光芒。它承载着人们的情感与记忆,是家乡的符号,是亲情的纽带。
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,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它记录着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,承载着人们的喜怒哀乐。在方言中,我们可以感受到先辈们的智慧与幽默,也可以体会到生活的酸甜苦辣。每一种方言都有其独特的韵味,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。如今,随着普通话的普及,方言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。然而,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瑰宝,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它是我们与家乡之间的桥梁,是我们心灵的归宿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,只要听到熟悉的方言,就会立刻感受到一种亲切与温暖,仿佛回到了故乡的怀抱。
方言是乡愁,它让我们在异乡也能找到归属感,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不忘来时的路。让我们珍惜方言,传承方言,让这份独特的文化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,永不褪色。
来源:茶陵融媒
作者:陈 欣
编辑:陈爽
本文为茶陵融媒原创文章,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。